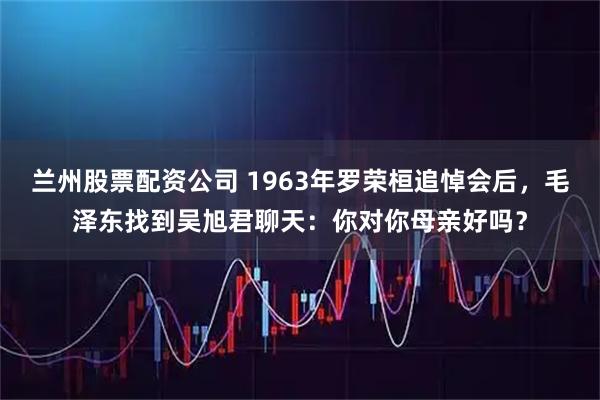
1963年12月18日凌晨五点,北京城笼着一层薄雾,灯火把中南海的石径照得忽明忽暗。追悼会已过去整整一天,可毛泽东仍在居室踱步兰州股票配资公司,茶几上的安眠药少了一半,窗外的松枝却没动分毫。熬过这样一个夜晚,他决定叫来值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。
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最先离开的一个,对毛泽东而言,那不仅是战友离散,更像一块连接长征岁月的基石突然塌落。1934年湘江激战后,两人曾对着地图研究突围线路,罗荣桓一句“慢一点,别丢人”仍像回声。如今,这位纪律严明又温厚的元帅成了遗像上的黑白微笑,毛泽东心里的洞便再也堵不上。
吴旭君推门时,他半躺在藤椅上,衣襟微敞。为了缓和气氛,她先把灯光调暗几度,再掂着壶续了水。毛泽东忽然抬头问:“最近给家里写信没有?”吴旭君没料到会被问起私事,愣了下,只说“已经寄了贺年片”。他又追问一句:“你对你母亲好吗?”

吴旭君从1953年起便守在主席身边。毛泽东对她的第一句玩笑是“’无细菌’这个姓氏好”,那时她才二十一岁。十年相处,让这位湖南老人把年轻护士当成半个女儿。可今天谈话显然与工作无关,他似乎更想探究一个儿女对母亲的情感。
毛泽东提到了自己的母亲文七妹。1893年冬日,文氏抱着刚呱呱坠地的长子,担心再失去,便回娘家湘乡,把婴儿与庵里一块石碑结成“认庙做干娘”的古怪缘法。毛泽东说时语气极轻,像怕惊醒谁:“母亲去世时,送殡的人排到稻田边,我却在长沙筹办学生运动,只赶上回乡跪拜,没见到她的最后一面。”

那一句“生不能尽忠,死不能尽孝”让房里更静。接着,他慢慢站起身,拿起桌上一册《形式逻辑学》,翻到扉页:“辩证法讲对立统一,有生就有死。罗荣桓去了,我也终有那一天。”声音低,却带着决绝。
1956年4月,国务院发起领导干部带头火葬的倡议,毛泽东第一个签名。当时不少老干部摇头,他只是说了一句:“土葬山河装不下。”七年过去,他仍惦记这张签名。那晚他告诉吴旭君,自己死后要火化,骨灰洒进长江,让鱼儿做最后一道“检阅”。吴旭君下意识抗拒:“太冷了。”毛泽东摆手:“自然规律,从来不讲暖不暖。”
说到这里,他突然咳了两声,又补了一句:“不希望你守在病榻前,我想让你留下活人的形象。”这番话令吴旭君鼻尖发酸,却只能轻声回答:“记下了。”一句话,很短,已够。
天快亮时,毛泽东让她回房休息。她关门前听见屋里传来断续的纸声——那是修改诗稿的动静。几小时后,《七律·吊罗荣桓同志》定稿,押韵依旧铿锵,只是墨迹颇重。
当日中午,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卫士鼓励值班人员照常锻炼,说话仍带笑意。可明眼人能看出,他的肩背较前些日子更显低垂。失眠、咳嗽、药片,老年气息一点点爬上去,连亲密助手叶子龙都没再多劝。
两个月后,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一份保健方案,核心是“减少夜间批阅”,可毛泽东从未严格落实。他常说:“事拖一拖会发霉。”这种性格,罗荣桓最懂。某种意义上,凌晨对护士谈生死,既是对朋友遗去的回应,也暗自为自己备下注脚——只是这一层,毛泽东没向任何人挑明。
1964年春,东风里已有柳絮。吴旭君翻看自己的工作笔记,看见那一页写着“12月18日,主席说人总要死,骨灰要撒江里”。铅字粗重,她想撕下,却终究摞好夹回本子。文件柜合上,锁扣咔哒一声,像在提醒:那一夜谈话的内容,只能锁在记忆里,不必对任何人复述。
2
涌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